全注全译史记
上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1995年3月第l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0-15000
ISBN7-80504-378-7/G.66
定价:330:00元
�
前言
《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汉代以
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
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
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
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
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揭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
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
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
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
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
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
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
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
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
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
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
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
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
年(公元前 110 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
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
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
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
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
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
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
(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
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
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
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
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
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
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
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
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
�
《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
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
往昔的阶段。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祕书,看似荣
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
辱。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终于超越了自我,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史记》
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
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
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
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去世年代,向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
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
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
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
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
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
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
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
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
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
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
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
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
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
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
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
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
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
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
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
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
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
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
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
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
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
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
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
�
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
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
书·经籍志序》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
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到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
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
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记》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两
种说法赞同者多,一说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一说终
于太初年间(公元前 104 年至前 101 年)。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历
时三千年左右。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史记》,从而使《史记》
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迁之前,也
出现过不少史作,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
本》、《秦记》、《楚汉春秋》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但这些史
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司马迁所处的
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文化勃兴。奋发昂扬的时代
气息,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汉兴秦亡,原因何在,
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再往上推溯,历代的
兴亡,都需要思索,寻找出规律,作为汉代统治者为政的借鉴。司马迁正是
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完成了他的史作,从远古,到当代,悠
远而恢弘,体现了汉武时期的辉煌。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
经过剪裁加工,才能镕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
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
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
《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的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
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
《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
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
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
《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
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
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
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
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
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
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
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
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
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
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
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
�
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
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
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
《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
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
与《夏本纪》、《金滕》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
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
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
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
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
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
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
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
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
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
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
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
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
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
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
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
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
“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
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
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
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
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
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
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究
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
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
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
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
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
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
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
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
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
�
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
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
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
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
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
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
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
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
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
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观衰”,“稽其成
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
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
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
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
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
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
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
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
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
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
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
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
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
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
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
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
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
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
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
“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
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
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
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
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
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
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
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
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
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
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
记》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
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
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
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
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
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张晏云:“迁
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
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
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
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
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
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
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
士褚少孙便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
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
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
《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
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
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诸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
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
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但同样缺乏确证。
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
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见载
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
《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
《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
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祕
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
《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
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
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
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注音,还注重释义,音义并重。张守节
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
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
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三家注本
来各自单行,宋朝时才把三家注统一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清人吴国泰
撰著《史记解诂》、瞿方梅撰《史记三家注补正》,多有新的阐发。今人日
本泷川资言撰著《史记会注考证》、台湾王叔岷撰著《史记祕斠证》,都是
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今天尚能见到的都是零散的
�
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时期抄写的《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篇和《史
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国内外藏有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
集解》。能够使《史记》得以广为传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后出现的
大量木刻本。北宋景祐年间,曾刻《史记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
图书馆。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
古老的刻本了。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
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无为州官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刻
本为最古,此本颇受学术界重视,涵芬楼和商务印书馆都曾影印。清代是整
理古籍的辉煌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流传较广的刻本,一种是乾隆
四年(公元 1739 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人们
称之为“殿本”。因为是国家一级的官刻本,所以有许多知名学者参加校勘,
对《史记》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另一种是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金陵书
局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此本汇校了宋、元、明有代表
性的各种版本,并汲取了学者的研究成果。此本失误较少,人们视为善本。
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开始标点校勘《二十四史》时,《史记》即采用金陵书
局本为底本。1959 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史记》。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两
个特点,一是全书有了标点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
札记》,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这次对《史记》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
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
本书的注释和翻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写就的,由于某些
原因,未能及时出版。这次付印之前,注释者又作了一些修订。由于本书成
于众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吴树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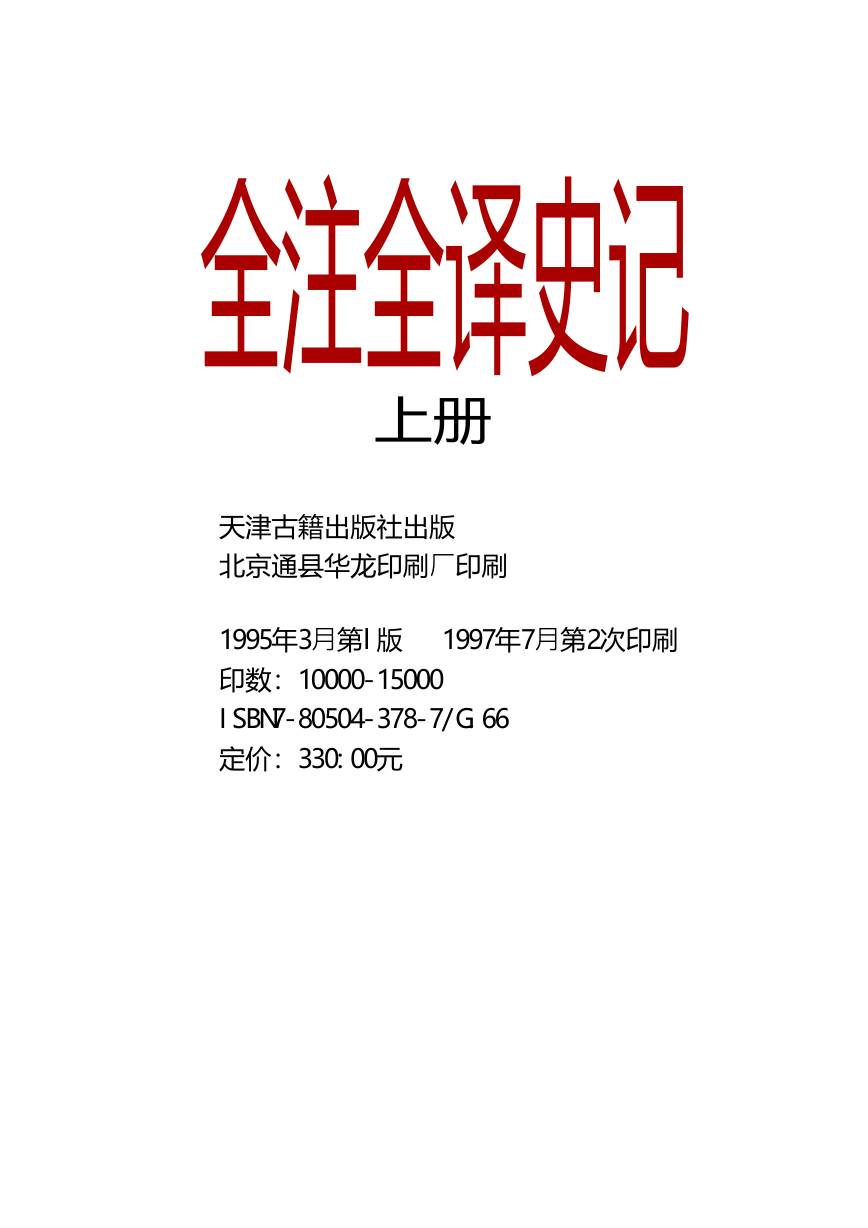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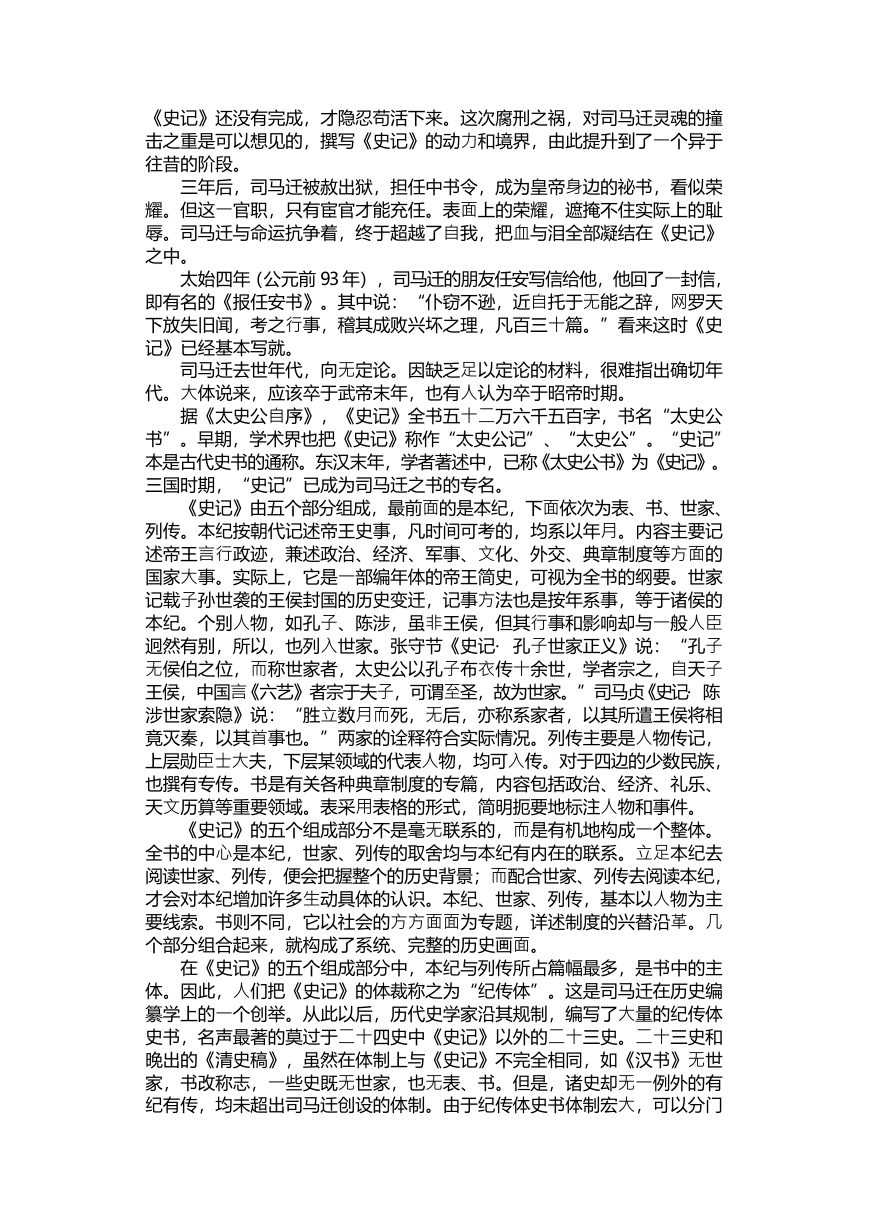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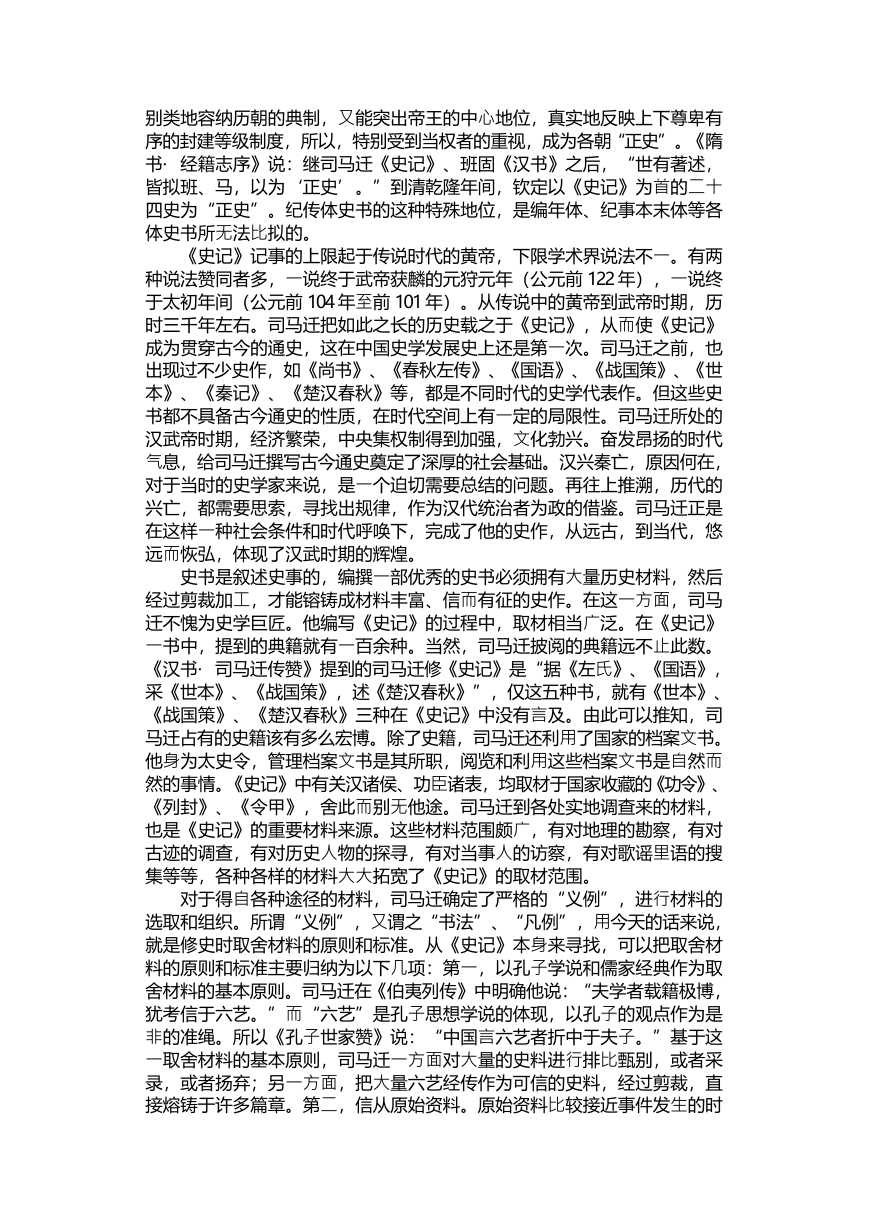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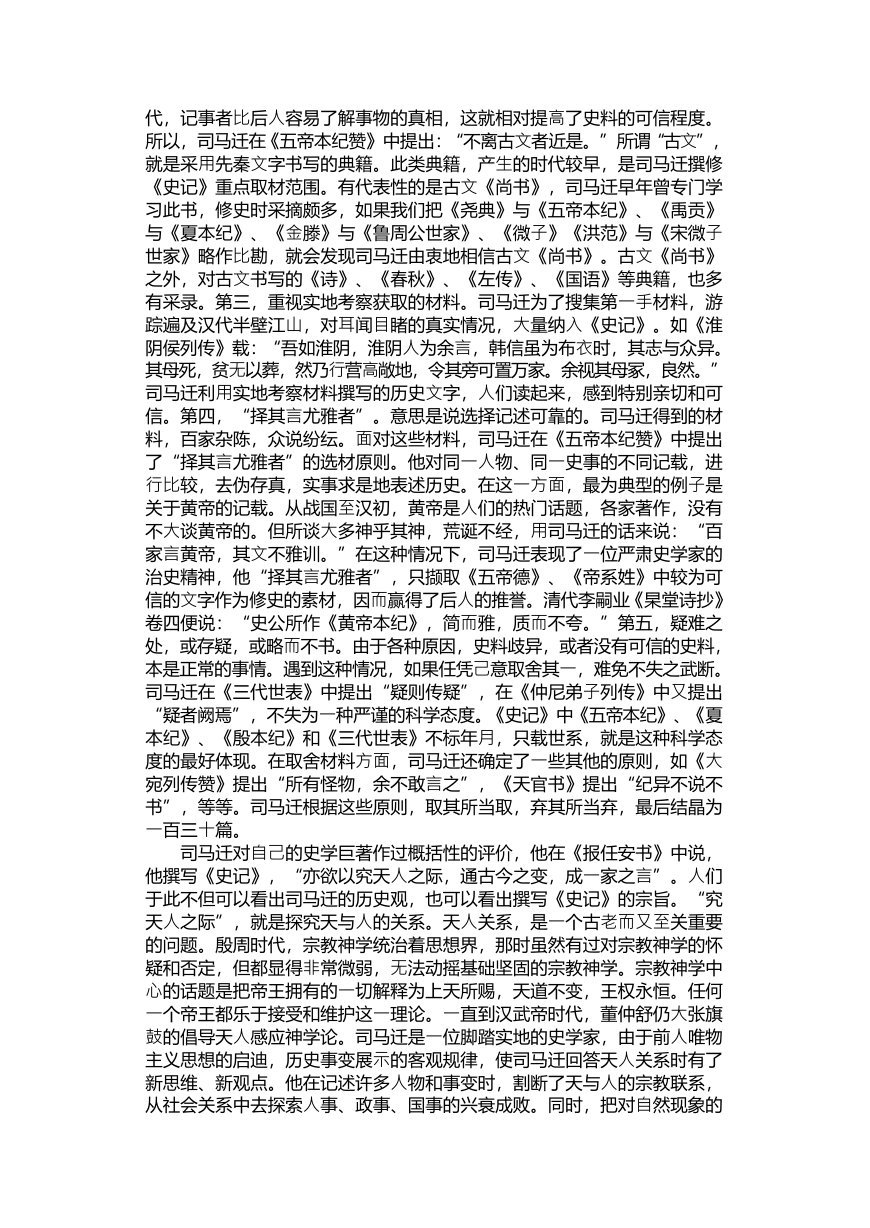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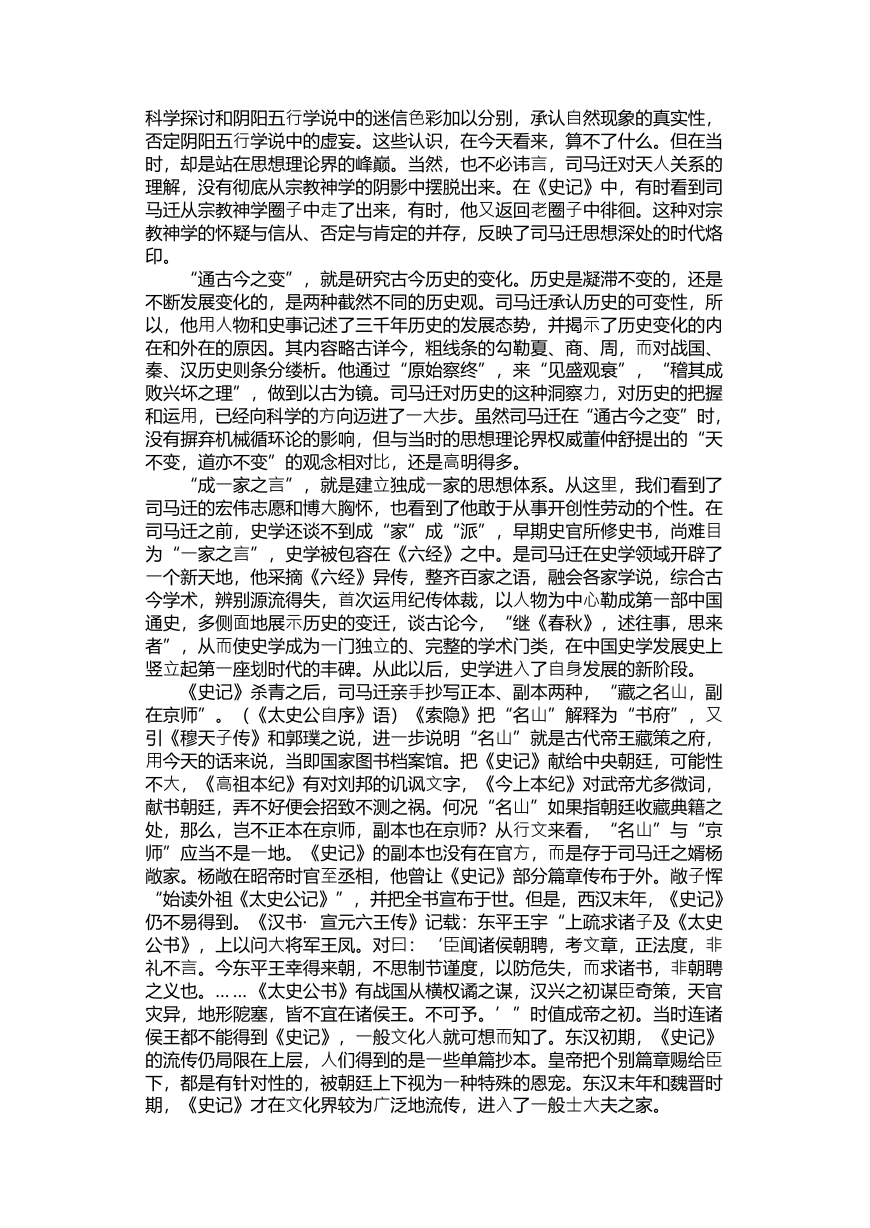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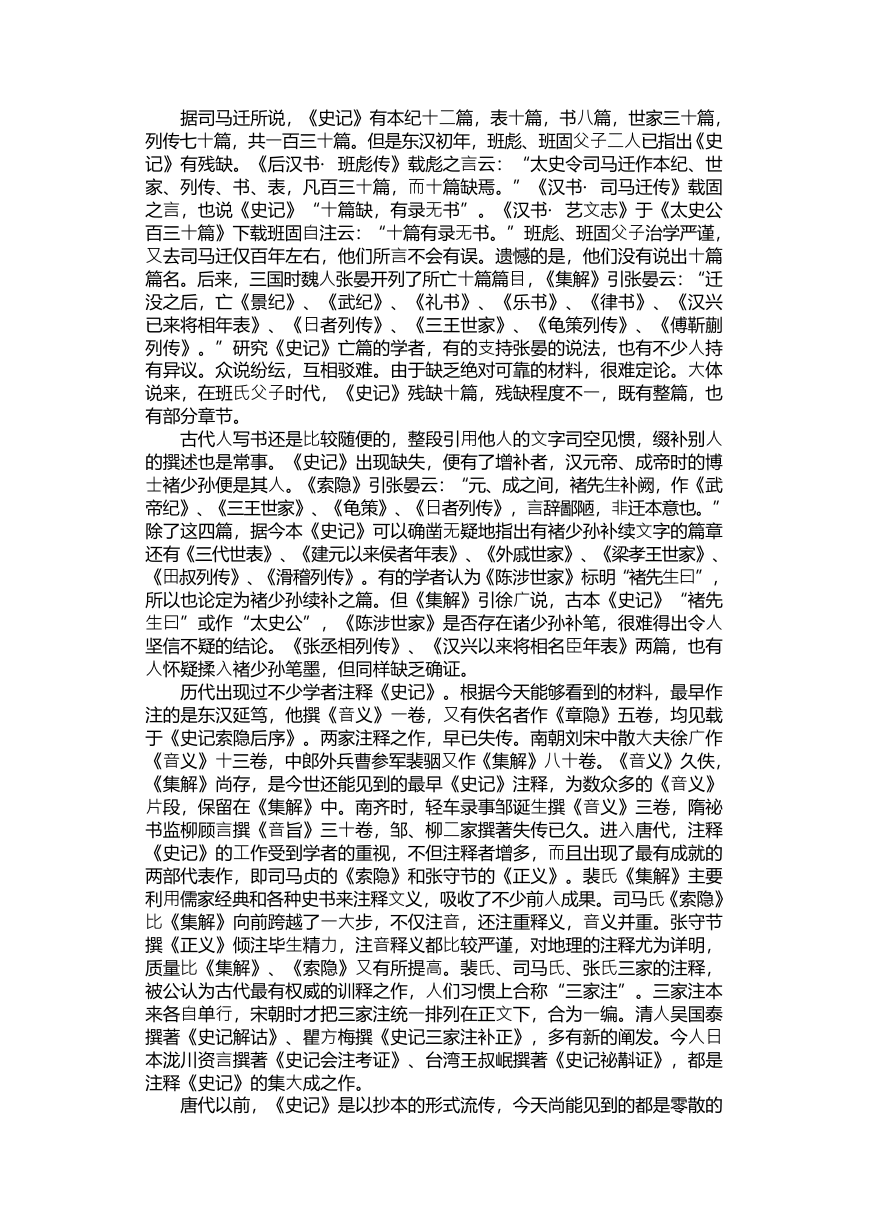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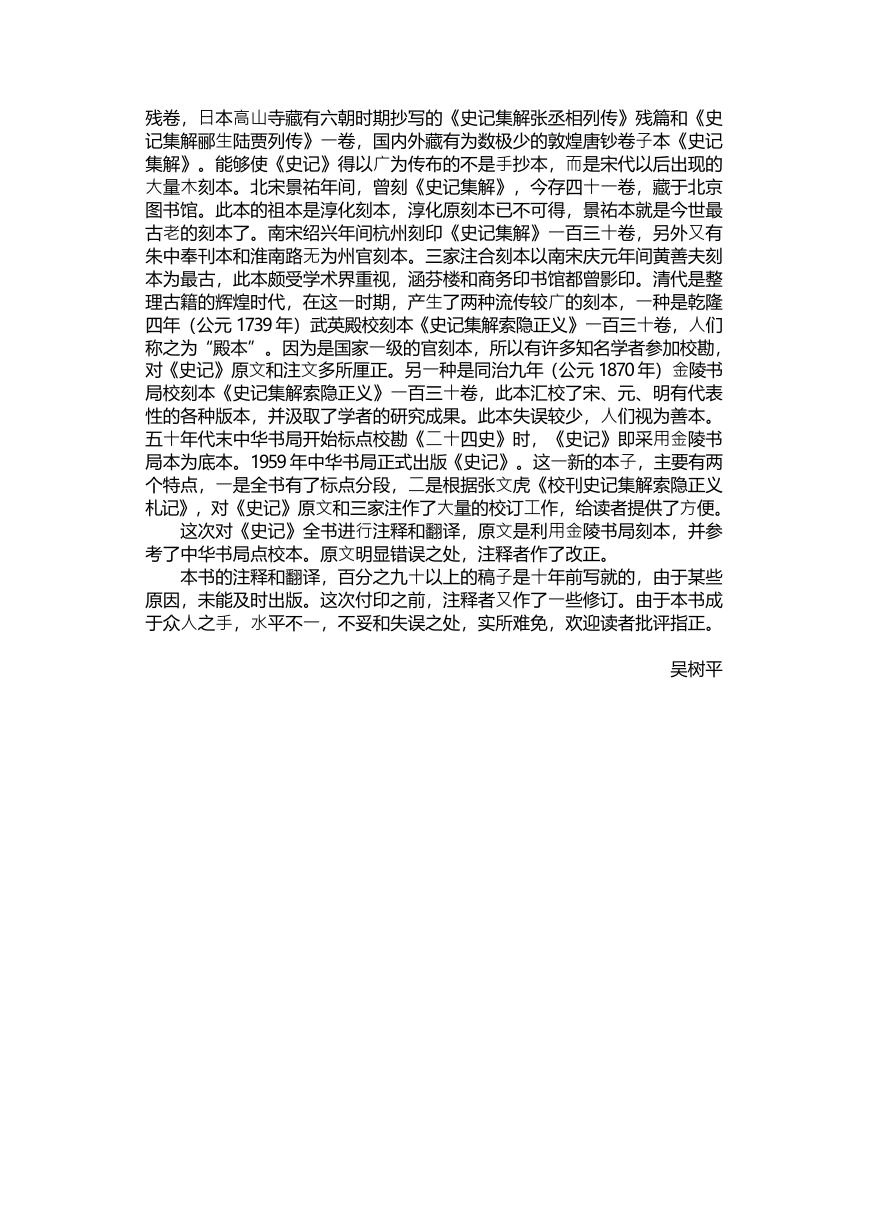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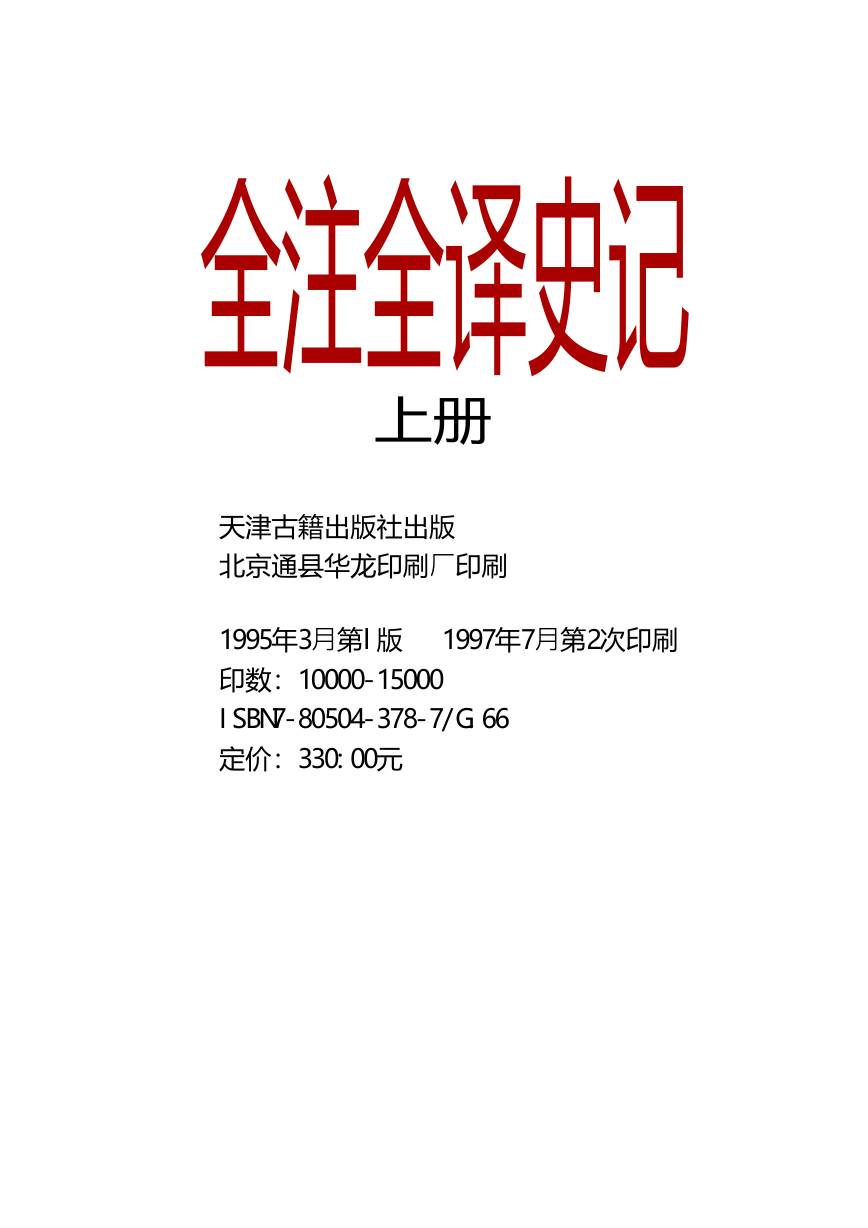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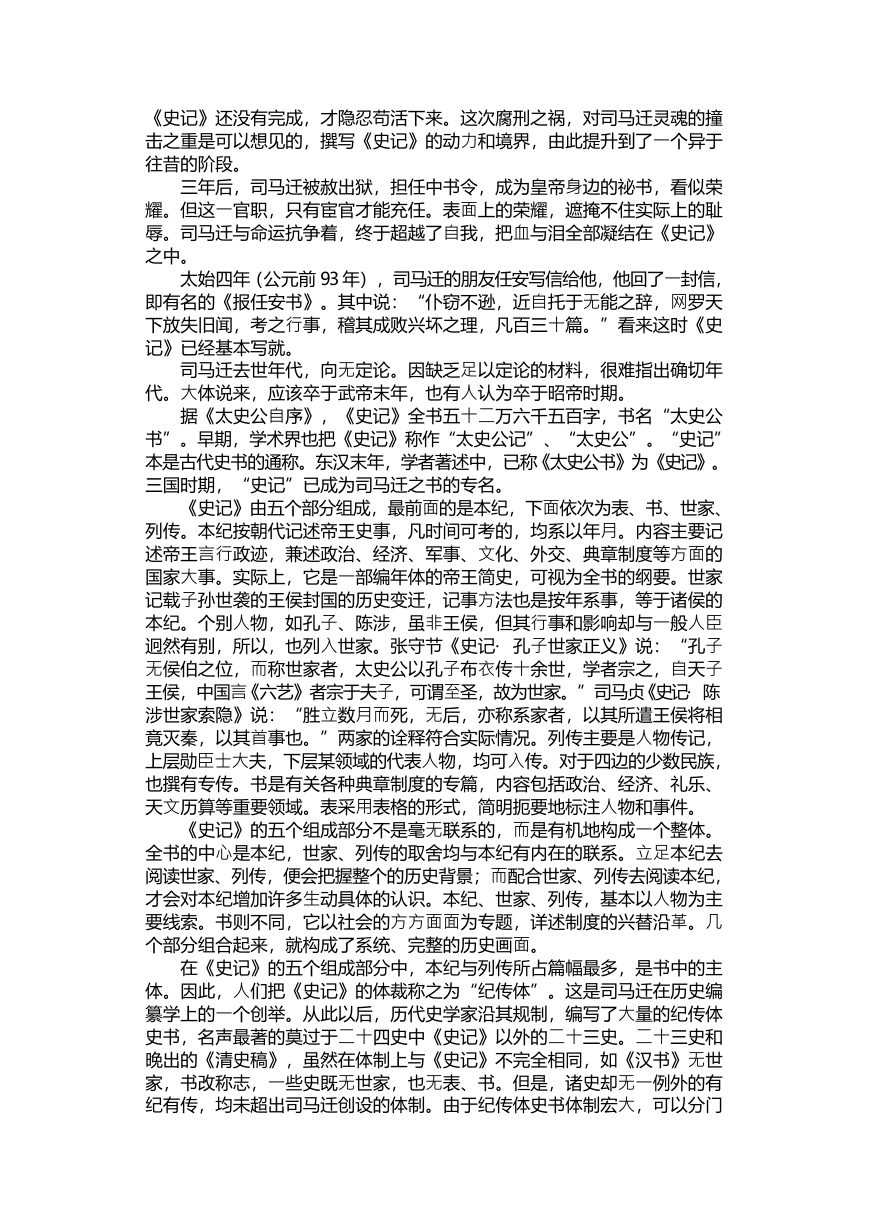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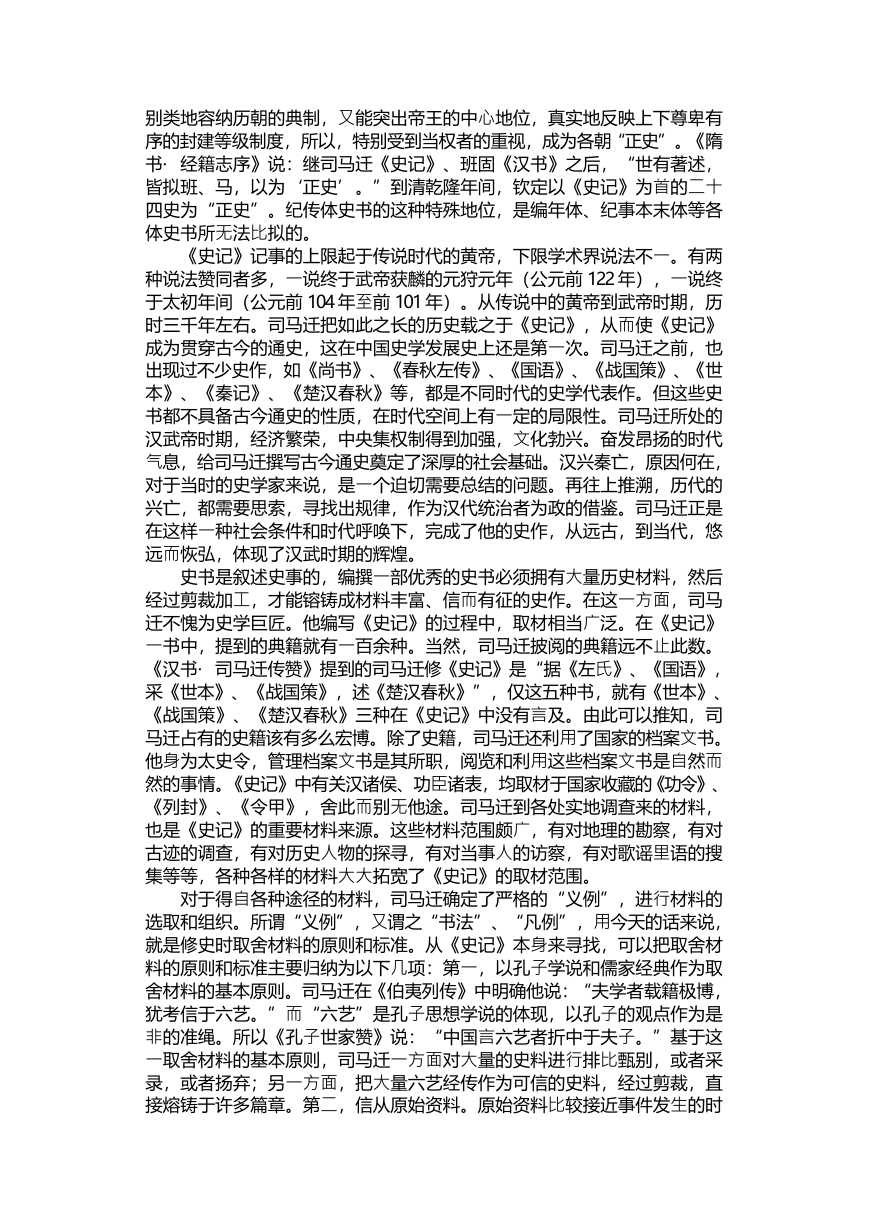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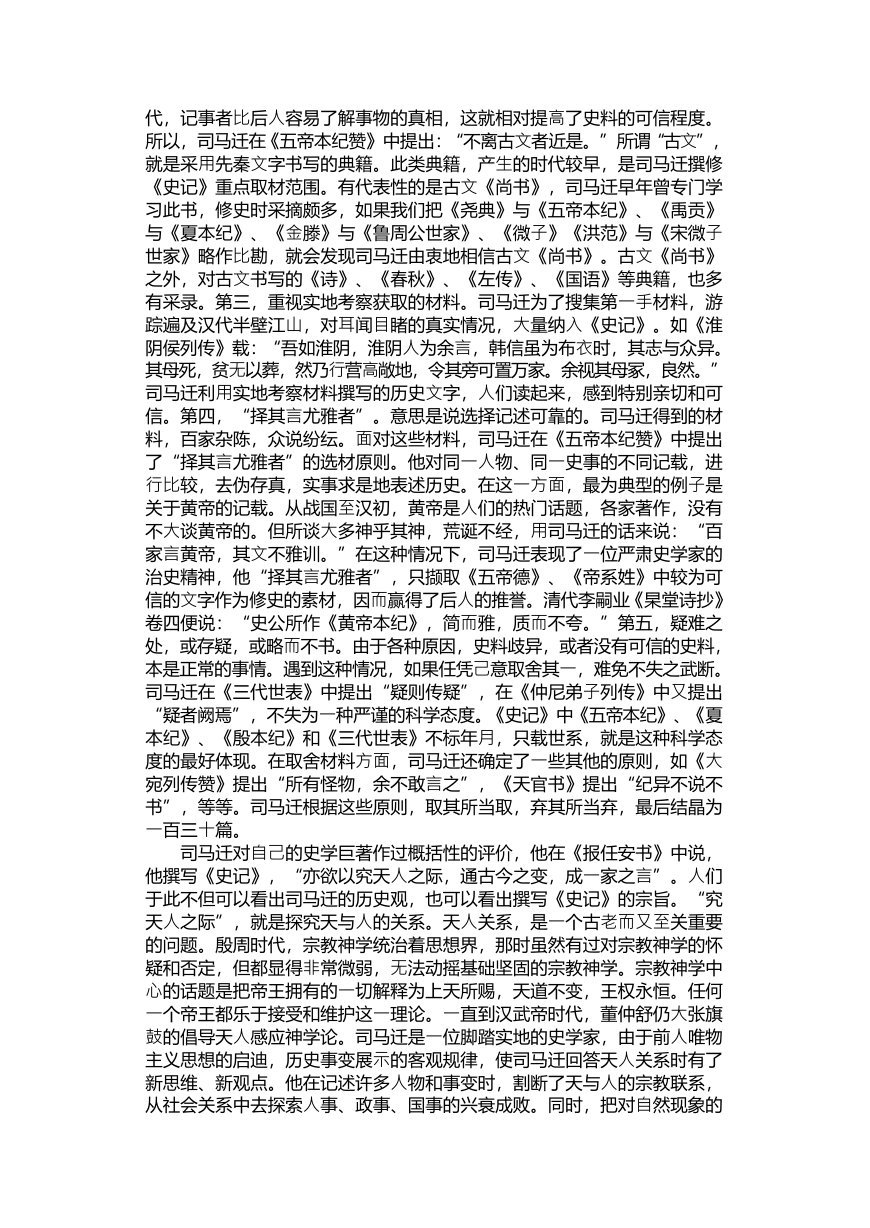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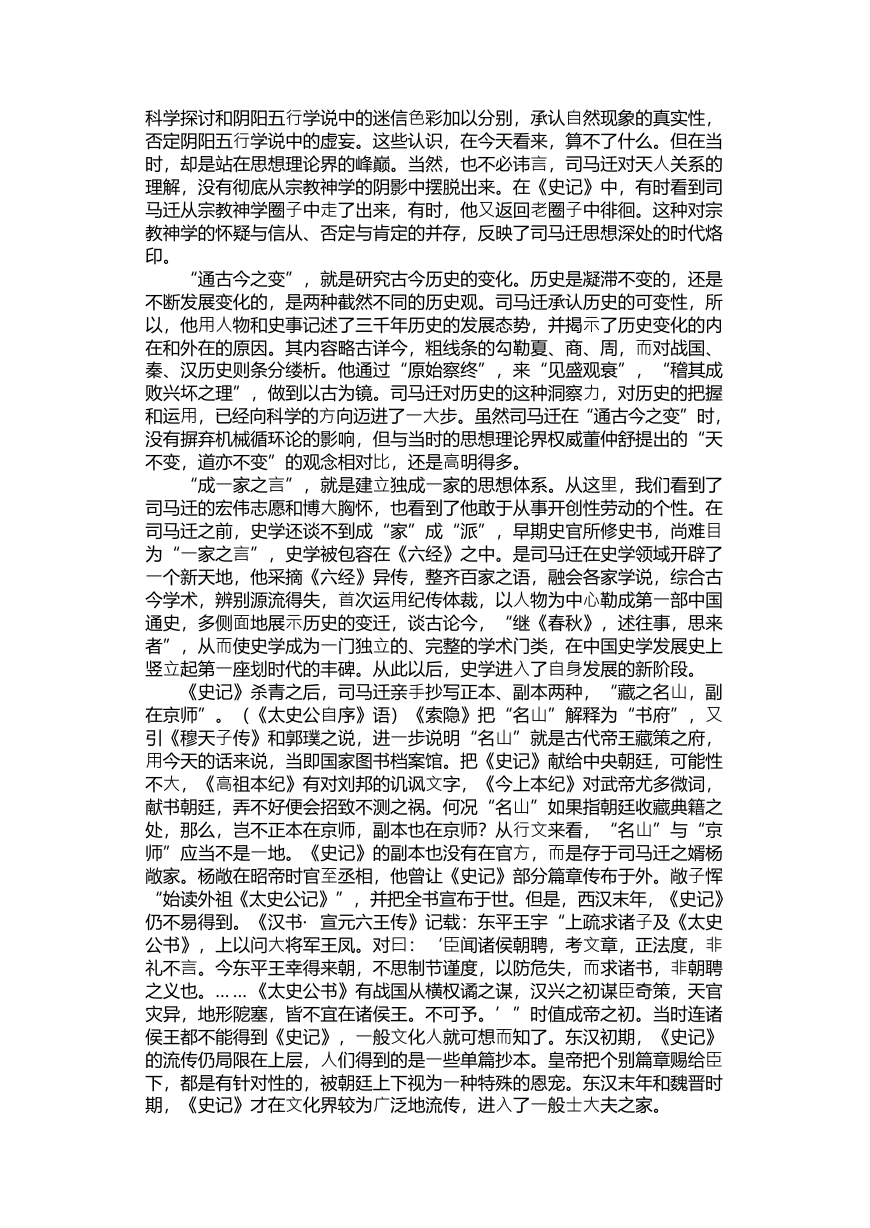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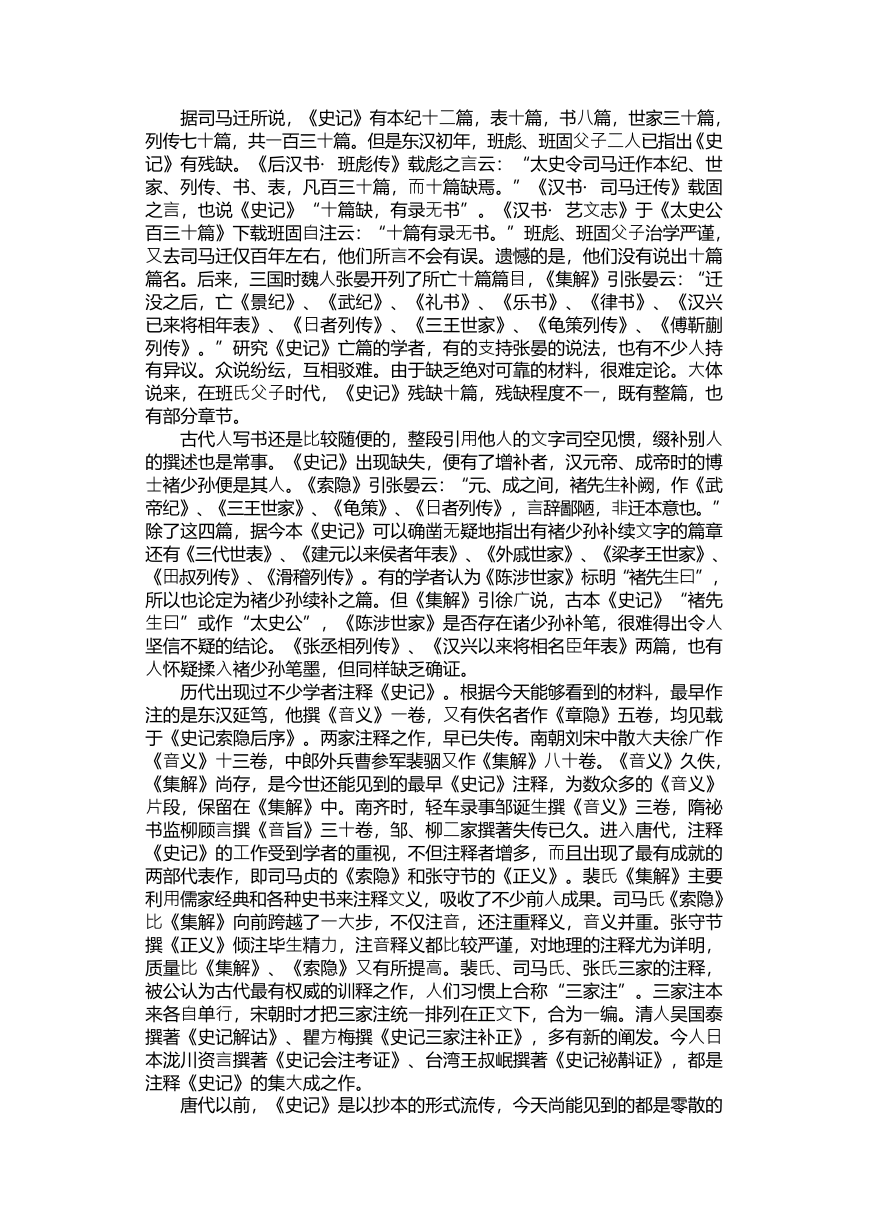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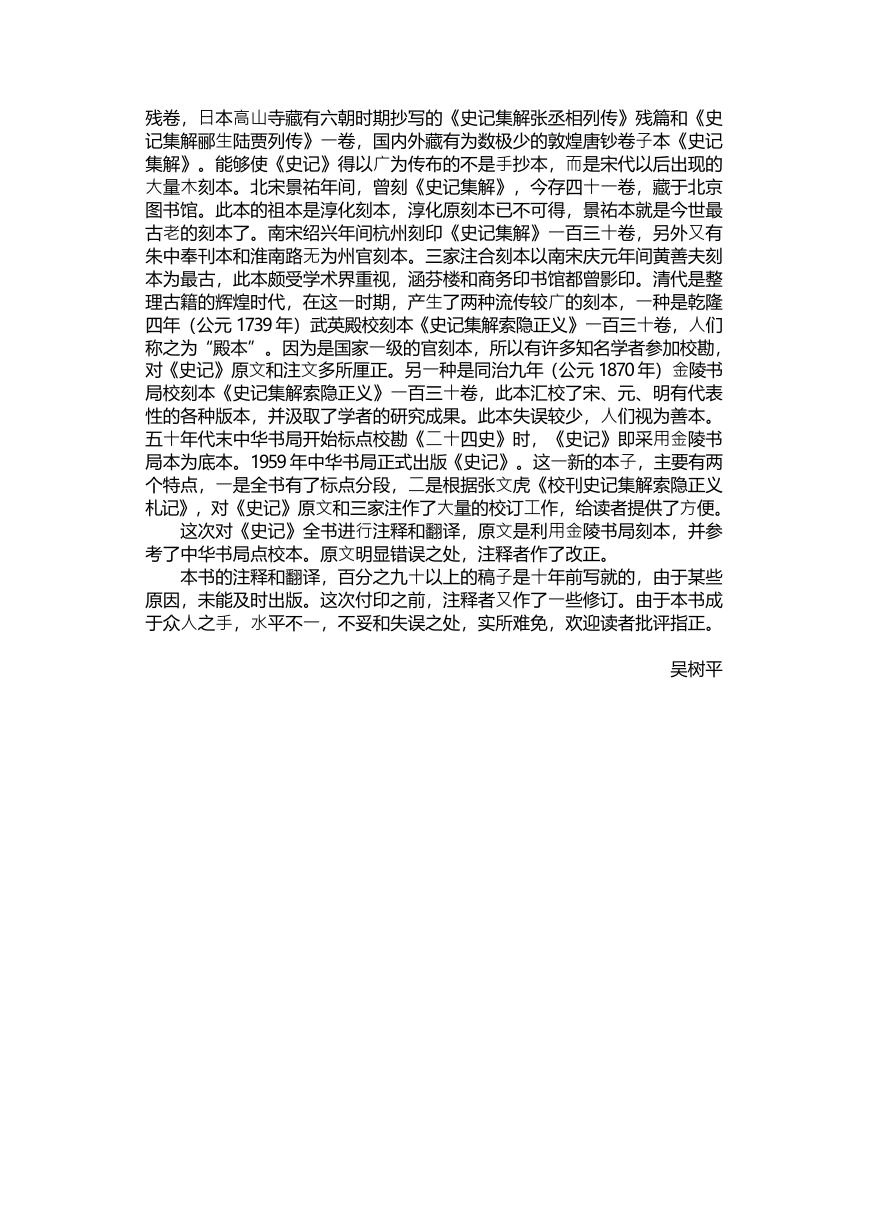
 2023年江西萍乡中考道德与法治真题及答案.doc
2023年江西萍乡中考道德与法治真题及答案.doc 2012年重庆南川中考生物真题及答案.doc
2012年重庆南川中考生物真题及答案.doc 2013年江西师范大学地理学综合及文艺理论基础考研真题.doc
2013年江西师范大学地理学综合及文艺理论基础考研真题.doc 2020年四川甘孜小升初语文真题及答案I卷.doc
2020年四川甘孜小升初语文真题及答案I卷.doc 2020年注册岩土工程师专业基础考试真题及答案.doc
2020年注册岩土工程师专业基础考试真题及答案.doc 2023-2024学年福建省厦门市九年级上学期数学月考试题及答案.doc
2023-2024学年福建省厦门市九年级上学期数学月考试题及答案.doc 2021-2022学年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期末试题及答案.doc
2021-2022学年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期末试题及答案.doc 2022-2023学年北京东城区初三第一学期物理期末试卷及答案.doc
2022-2023学年北京东城区初三第一学期物理期末试卷及答案.doc 2018上半年江西教师资格初中地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真题及答案.doc
2018上半年江西教师资格初中地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真题及答案.doc 2012年河北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真题及答案-省级.doc
2012年河北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真题及答案-省级.doc 2020-2021学年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樊片九年级上学期数学第一次质量检测试题及答案.doc
2020-2021学年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樊片九年级上学期数学第一次质量检测试题及答案.doc 2022下半年黑龙江教师资格证中学综合素质真题及答案.doc
2022下半年黑龙江教师资格证中学综合素质真题及答案.doc